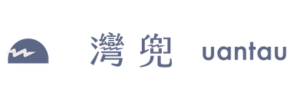一日三餐(或兩餐),若經常外食,最苦惱「待會吃什麼」。婚後開始日日自煮,省去覓食的選擇障礙,卻保留了吃麵攤的習慣。年少太彆扭,覺得獨自坐在麵攤吃麵看上去很寂寥。只有一個胃,豆乾海帶或肝連總要學會割捨,實在太沈重。不如一份三明治或一盒便當,不做他想。
認識先生後,才開始經常吃麵。兩個胃剛好,偶爾還是得抉擇,但已經夠貪心。十多年前董事長樂團有一首歌〈心愛的牛肉麵〉,講煞到麵店老闆女兒而常常去吃麵的故事,指的就是大名鼎鼎林東芳。我們去排過一次隊,很興奮要朝聖歌中的傳說,當時麵店還沒搬家,在低矮室內吃一碗牛肉麵加牛油,配上吸飽湯汁的花干。時光一去不回頭,物價也一去不回頭,牛肉麵早就不如歌唱的「一碗六十塊」。偶爾經過窗明几淨新店面,還是好奇,老闆女兒現在成為什麼樣的人?
說起吃食,老台北先生總有滿腹故事可講。難免面臨「你想吃什麼」窘境,互相揣測彼此提案究竟是遷就或有幾分真心。某次他靈光一閃,驅車到老字號福德涼麵。好吃麻醬麵難尋,偏又不像是值得翻山越嶺去探索的品項。福德涼麵很中我的胃,濃郁花生香及蒜味,淋幾瓢辣油,再熱也要飲一碗熱滾滾味噌貢丸蛋花三合一。先生邊吃邊說,年輕時夜唱結束就習慣三五成群到福德來墊墊略感空虛的胃。
如今早沒有夜唱的體力,福德小小店面仍容納川流不息狂歡後的青年,迷你裙高跟鞋、濃密假睫毛、眼影亮粉散落雙頰。深夜麵店映照出城市歇睏與起身的交界,來客除了填飽肚子,更多一分最後續攤的意猶未盡。
特別喜歡深夜的台北,車流稀疏,人步緩緩,影子長長。我們常漫無目的驅車閒晃,找一間熬滾大鍋白湯的攤,就著淒淒白燈泡,吃一碗陌生的麵,切一碟闊綽小菜。同居一室,難免齟齬,無心煮食,但飯總是得吃的。好幾次,反覆夾拌起了乾屑的麵條,沈默中嚥下和解的滋味。
第一次去東引小吃店,入夜後的松山菜市場陷入深睡,唯路邊一攤鹹水雞鴨亮著黃燈泡。左轉進東引所在的小巷,燈火通明,人力利索招呼擦桌,幾張小桌沿著路邊擺開,店面人聲鼎沸。完食後不過半夜三點,鄰近肉攤擺上整頭豬隻待天色亮起被切割出售。鋪著防水布的鹹水雞鴨攤剛賣出最後一盒,準備收攤。

雙北有數家我們慣吃的麵,最愛去的則是先生年少回憶之一四鄉五島馬祖麵,店裡招牌黑麻麵是用黑芝麻磨成的濃稠拌醬,盡責扒附著麵條,賣相不佳,是澈澈底底的麻醬對決,香的。這間店 24 小時營業,深夜常見計程車司機騎樓低頭吸麵,唏哩呼嚕嘴巴一抹,斜身上車如流星撇過紅綠燈號,繼續兜轉載客。


我們各種時段造訪馬祖麵,下午、傍晚、深夜及清晨,幾乎是同樣的菜色:黑麻麵炸醬麵各一、餛飩湯,切花干紅糟肉大腸頭豆干。偶爾麵條會改成同為黑芝麻醬製成的黑心水餃。如此死忠,美味是其一,安全感是其一。途中我不知嘗過多少家麻醬麵,受創程度不一,還是得委屈地回到馬祖麵療傷。
去年雙北三級警戒,每日自煮,最懷念的就是這些麵店。因此一解封,立刻前往吃一碗現煮的魂牽夢縈的麵,暗暗嘆息,人在一座城市有慣吃的麵,才像有了根。
本文刊載於〈城市學〉專欄,出處:《文化快遞》7 月號 no.26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