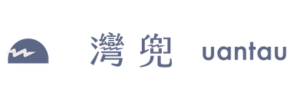工作常做採訪,幾天前被問起最喜歡採訪什麼樣的人?不假思索,就是那些看上去平凡無奇,與你我無二致的一般人啊。街邊烤酒釀餅的攤販、背對一整排過時鮮豔衣褲倚著櫃檯打瞌睡的老闆娘、身著熱褲網襪長假髮疾走的老伯、將臉抹得粉白宛如日本能劇等公車的少女…,每一天我都得壓抑著去與他們攀談的衝動,久而久之,心底壓了份「採訪遺珠圖鑑」:
花塢仙子

為著送一份小禮,來到中山堂附近一間花店。狹長型店面被盆栽冷藏櫃塞滿,櫥窗假花盆透露二十年前的審美,敷著薄薄的灰,屋簷廊梯擺滿小盆栽。一位阿姨閃身而出,素色長裙配繡花鞋。問她這是什麼?阿姨站高一階,母儀天下,不冷不熱,答,那是合果芋。
選定盆栽想換容器,阿姨表情微微困擾,「這樣我還要換土。」(即使有另外收費)不似生意人熱呼呼,有種「要買便買吧,都是好的。」的泰然。所幸她還是飄然穿過葉葉枝枝進去換土了。
趁隙東看西看,店名「蝴蝶蘭花塢」古典文雅非常,招牌設計想來當年十分新潮時髦。猜想阿姨也許一生專心與花草打交道,繡花鞋自然不必沾染塵土。後來換了店員捧著盆栽出來收錢。花塢主人又隱身枝葉間,真正仙氣。
街頭者
從西門走至 228 公園途中有不少常駐街友及乞者。一位慣習蹲踞銀行前的阿伯,染滿頭黃髮。熟透香蕉的那種黃。一兩週後,髮色換成帶紫豔紅,髮絲表面覆著層塑膠光。(確定那是真髮,隔段時間便有布丁)疑心是哪兒染的呢?衣衫襤褸卻堅持染髮,染得那樣均勻,應該是上髮廊吧?
衡陽路與博愛路交叉口騎樓,總有一名面具者席地拉手風琴,席前有打賞盒,一旁紙板寫「盲眼阿伯高蹺走天涯」。正午時分上班族傾巢而出,悽悽樂聲是漫長紅燈的背景樂。大夥提著便當麵羹背對琴音,無人打賞。突然染髮阿伯走來,遞出一瓶無糖冷飲。面具伯連聲道謝,說別再買啦。染髮阿伯擺擺手,一頭赤焰紅髮隱沒街角。號誌燈綠,人人前行,交叉,前進。
凱蒂理髮

公司旁有間神秘的理髮廳,建築是古早的派頭,玻璃門曖昧的高度橫跨著一張貼紙,每天經過我放慢速度伸長脖子,裝潢老派昏黃,整齊理容椅一字排開。不是給一般婦女做頭髮的店,沒見過女性造訪。只看過一名禿頂阿叔躺著,下巴爬滿刮鬍泡,年過半百的阿姨為他剃鬚。
裡頭的阿姨都有年紀。偶然碰見她們屋簷下洗水桶,雙頰有風霜,素淨家常,很像是誰家的舅媽。這理髮廳到底在這多久了?平素客人不多如何營生?一把剃刀刮鬚髮,失手過嗎?曾不小心抹出傷來嗎?昏黃燈光下曾經覺得哪個男客颯爽如初戀嗎?
左想右想,該用何種方式接近她們。琢磨許久才在心中定案,應該守株待兔等有人出來,便故作天真問:「姊姊,可以洗頭嗎?我想要洗頭~」若沒被拒絕就進去洗吧,一回生二回熟,大不了兩天去洗一次,洗著洗著總會熟起來吧,就能聊天吧。
暗自肯定自己的計畫,邊期期艾艾伺機而動。想沒到,上週經過緊閉鐵門貼著一張搬遷啟示,我差點哭倒長城。就好像,你暗戀隔壁隔壁班女生很久,好不容易鼓起勇氣要去告白,到了她教室門口才發現她前天轉學了。
本文刊載於〈城市學〉專欄,出處:《文化快遞》12月號 no.27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