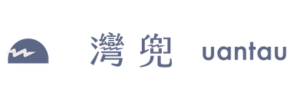民俗以外,推理小說與各種未解疑案,也都在唐墨守備範圍。談到他與推理的結緣,就得把時間從童年快轉到他的學生時代。
本來算是乖乖牌的他,高中參與過校刊社,讀的都是師長推薦的經典文學,一度對推理小說嗤之以鼻。不曾想後來接觸阿嘉莎‧克莉絲蒂的作品竟一頭栽入推理的世界。
閱讀清單還包括福爾摩斯、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和松本清張,只能說乖乖牌認真起來,經典、現代都一網打盡。
當中,松本清張的《天城山奇案》,這部致敬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孃》的中篇小說,把原本只是鄉野傳奇等級的故事寫成了精采的謀殺案,還詳細刻畫青少年的心理變化,打開了唐墨對推理小說的想像。

我想寫的,是「只有我能寫出來」的推理小說
多數創作都從模仿開始,唐墨仿效《天城山奇案》結構,將故鄉的草嶺古道融入創作寫出《蠱道之口》投稿蘭陽文學獎,一舉獲得名次,讓他意識到「地方特色結合推理是可行的。」
可行還不夠,「我想找出別人沒辦法做到,只有我行的題材。」唐墨舉例當時早期守娘這些鄉野傳奇還沒人寫,他注意到臺灣有清代三大奇案、四大奇案甚至到日治時代延伸為十大奇案,看似荒煙蔓草,其實都是待被翻掘整新的寶藏。
「只有我行」恐怕是許多創作者難以繞路的執念,也昭示某種自信,以及自身的孜孜矻矻。
筆者不自主想到最初在寫《除念師阿平》,這部講述除念師如何動手協助常人解決放不下的執念,靈感很多都來自年輕時網路討論板讀到的親身經歷或無法解釋的事件。那些像都市傳奇的故事雖然短卻後勁十足,同樣憑著「只有我能辦到」的心情投入創作。
然而,如何選定那「只有我行」的題材?又如何辨識那究竟是能燃出新火的死灰,又或者真只是一堆廢土?唐墨舉了十大奇案的「二林石阿房奇案」為例:
沒有監視器、矢口否認就死無對證的日治時代,為財起殺心假裝要從二林買花生回新竹販賣的農人盧章,揪有錢的石阿房合夥,最後將石阿房用木棍打死。懸案本來就要停在這了,但盧章卻沒事將石阿房的金錶取下送給情婦,最後被日本警察察覺不對勁,演了一齣冤魂索命的戲終於讓殺人兇手說出實情。
「我讀到這個故事時,真的覺得很北七,怎麼會有人這麼做,可是報紙就是這樣寫。其實它很有能量,只要適度地改寫,一定可以寫成現代人看得懂並接受的故事。這就是我想做,也是我能做的。」
每個社會案件,都具有自己的時代意義
「台灣股票淹肚臍/台灣厝價淹下骸
——沈文程〈1990台灣人〉
台灣槍子淹目眉/台灣人的心事無人知
古早時袸就有歹人/只不過作法甲今嘛嘸啥同
厝內的某子你著好好阿藏/哪無乎人抓去一個一個綁
大頭家想著目眶紅/歸去來去買一支ㄅ一ㄤˋㄅ一ㄤˋㄅ一ㄤˋ
莫怪許桑對咱大家共 出門小心不要踩到槍」
每當有重大案件發生,總會有網友留言:「以前治安好多了。」但事實真是如此嗎?沈文程一曲〈1990台灣人〉描述當年社會亂象,「出門踩到槍」這句歌詞就出自於真實典故。
由於 1980 年代台灣治安不佳,時任內政部長許水德於立法院備詢,當立委砲轟黑槍氾濫,只能回應:「這幾天我們出門走路真的會撿到槍」。
比起歌曲更殘酷彰顯當代社會風氣的,無疑是真實案件了。
觀察各類型自媒體或頻道平台,會發現犯罪實錄或懸案調查,一直是有穩定流量的題材。然而為什麼大眾喜歡閱聽,除了出自於對罪的好奇、窺探,對筆者來說,一樁案件,往往是特定時空背景及社會風氣下的產物。
「疑案辦」(重大歷史懸疑案件調查辦公室)致力於研究和調查被遺忘在歷史卷宗的懸疑案件,唐墨也在平台中開設專欄,以現代角度重新調查詮釋武漢大旅社事件、七彩藝苑殺人等台灣重要案件。今年疑案辦受邀到社區大學開班,授課主題就是透過社會案件認識台灣。
好比廣為人知的李師科案,發生於 1980 年代,是台灣治安史上首宗「殺警奪槍、再搶銀行」的案件,背後卻凸顯出外省老兵安置、貧富不均、警界刑求陋習等社會問題,必須親臨時空,才能深刻了解驅動悲劇的推力。
換位思考,在梳理案件時同樣重要。唐墨舉十大槍擊要犯之首林來福為例,誰也沒想到一名小弟見到老大買香腸不付錢,上行下效最後竟然會演變成一場兇殺案,一路逃亡又有人提供槍枝,最後成了震驚臺灣社會的通緝犯。不若大眾想像的血海深仇,到頭來竟只是出自「模仿」二字。
如果僅是站在原地,不去探查犯罪者心理,不去爬梳案件的成因,社會案件終究只會是一樁善惡二分的罪行,無法從中探見更幽微的內核。
藏在犯罪案件背後的事實,是每個人都想打開的潘朵拉,但所謂的事實究竟如何?又該怎麼透過內容重建「事實」?成了寫作者田調的考慮要素。

2023年唐墨出版小說《腥紅速寫》,改編自 1986 年臺灣第一起隨機連續殺人事件「陳高連葉連續毒殺七名學童事件」。唐墨在田調時發現這起案件背後隱藏的是1980年代的女性處境,即使時代已經在進步,可是社會對女性的壓迫、精神障礙及產後憂鬱的污名仍無所不在。
為了凸顯當下時空背景,他刻意在書中安排兩位教育程度差異懸殊的女犯人與學者,展開一場名為犯罪事實的側寫實則為獵人遊戲的競逐。
田調的雜訊,寫作的底氣
然而,如何去理解一位犯罪者的心路歷程,成了田調時最棘手的難題。
民俗與真實案件的田調方向完全不同,大量查閱舊報紙是改編社會案件的功課之一,其餘則有賴於親自走進田野,從細節重建時空與社會氛圍。
唐墨坦言原本的案件至今已經三十餘年,許多人事物已隨著時間流轉而消失或抹滅。他在田調期間實際拜訪枋寮,為了搞清楚地理條件,特地跑一趟戶政事務所查詢門牌號碼,也去看過當地的房子,經過在地人指認再從門面的華麗進一步推敲當事人及夫家的社經地位。

小鎮最容易聚集人潮的媽祖廟口自然也是訪查重點,許多畫面則是問出來的。他如此形容探問當地人對該案件的記憶時的過程:「這個案件很久了,一旦有人問,他們腦中那個 CPU 就會開始轉動回憶。」
擱置多年 CPU 難免卡頓,他幽默形容有些受訪者會產生曼德拉效應。比如犯罪者當年的還小的兒子早已被出養到國外,卻有在地人記憶錯置,以為他還在台灣等等。
記憶是真實揉雜虛構的產物,田調的意義之一,也許就是盡可能考究真實,才能創作出不偏離現實的內容。
田調如同經營一段關係,有時該主動,有時適宜欲拒還迎。唐墨分享採訪撇步,藉著閒晃引起地方耆老的注意卻不急著開口詢問。走一次不夠就走第二次,第三次上前打招呼已經釣足對方胃口,把所知的全盤托出,正中下懷。
「你所蒐集到的這些訊息很像雜訊,弄懂了也沒好處。雖然看起來跟主體事件無關的,堆疊起來卻是重要的背景資訊,可以幫助寫作者快速地建立概念,傳達正確的訊息。」
說穿了,每位寫作者只要進行過田調,心情應該都七上八下。做好的功課能夠用上的不多,可這些看似無用的功夫,不只是搭出一座接近現實的舞臺,更是一種拍胸脯掛保證的事實擔當,屬於寫作者給自己的底氣。
有了這些雜訊,角色才能從容上台,而這些蒐集而來的事實,提供了推敲受害人與加害者的關係與心路轉變的證據。
「這個世上沒有一個人是認為自己在做壞事,很多人其實是存著好心但把事情做壞,寫作必須要把這種想法透過行為與對話的互動傳遞出去。」
即使是犯罪者也有讓讀者共情的質地,即使他十惡不赦,若能有讀者從他故事中看見自己的經歷,作品中人性的厚度便就此開展。唐墨強調,描寫一個人的過去不是為了合理化犯罪者的行為,而是找出犯行背後真正的癥結,逸出人倫綱常的一連串因果。
寫作的意義是什麼?創作者想說的又是什麼?與其說期盼寫出精彩絕倫的高潮起伏,到頭來已逐漸轉變為希望讓筆下人物好好地活一次。無論虛構或奠基於真實,都應該被看見。
洞悉並能寫出那些卡榫人事物的因果,或許就是讓人物「活一次」的還魂水。
今日的小傷小痛,原來是累世的福報
明星咖啡廳對面是臺灣省城隍廟,受訪之前,唐墨先去廟裡參拜。原來出家人也會拜拜嗎?經他說明,才知道城隍廟裡的觀世音菩薩,原本被棄置在路邊,後來輾轉來到城隍廟,形成了佛道共享香火的場面。

台灣佛道不分家,精神核心卻大不同。唐墨分享了佛教「重業輕報」的概念,讓平常接觸道教文化慣了的我感覺十分受用:
「今早撞到手,想求佛菩薩讓我的手別這麼痛,可是轉個念想,佛菩薩修行這麼久,可不是為了解決我這種雞毛蒜皮的小病小痛。況且或許本來是很嚴重的劫,卻有累積好幾世的福報分攤,到現在才變成這樣的小傷,這樣想來就豁達了,也不覺得苦了。」
不苦的唐墨,大概是經過好幾世的福報才能用爬文字的方式,付出有點苦味又能回甘的手痠與兩眼昏花,為故鄉、為現在腳下的土地繼續寫故事。雙手合掌,期許今天也要感性與理智合一。
唐墨《臺北男神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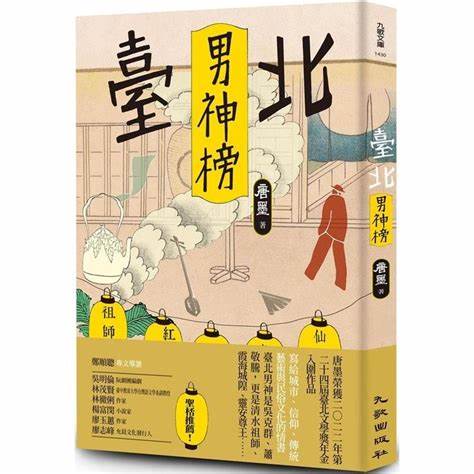
《腥紅速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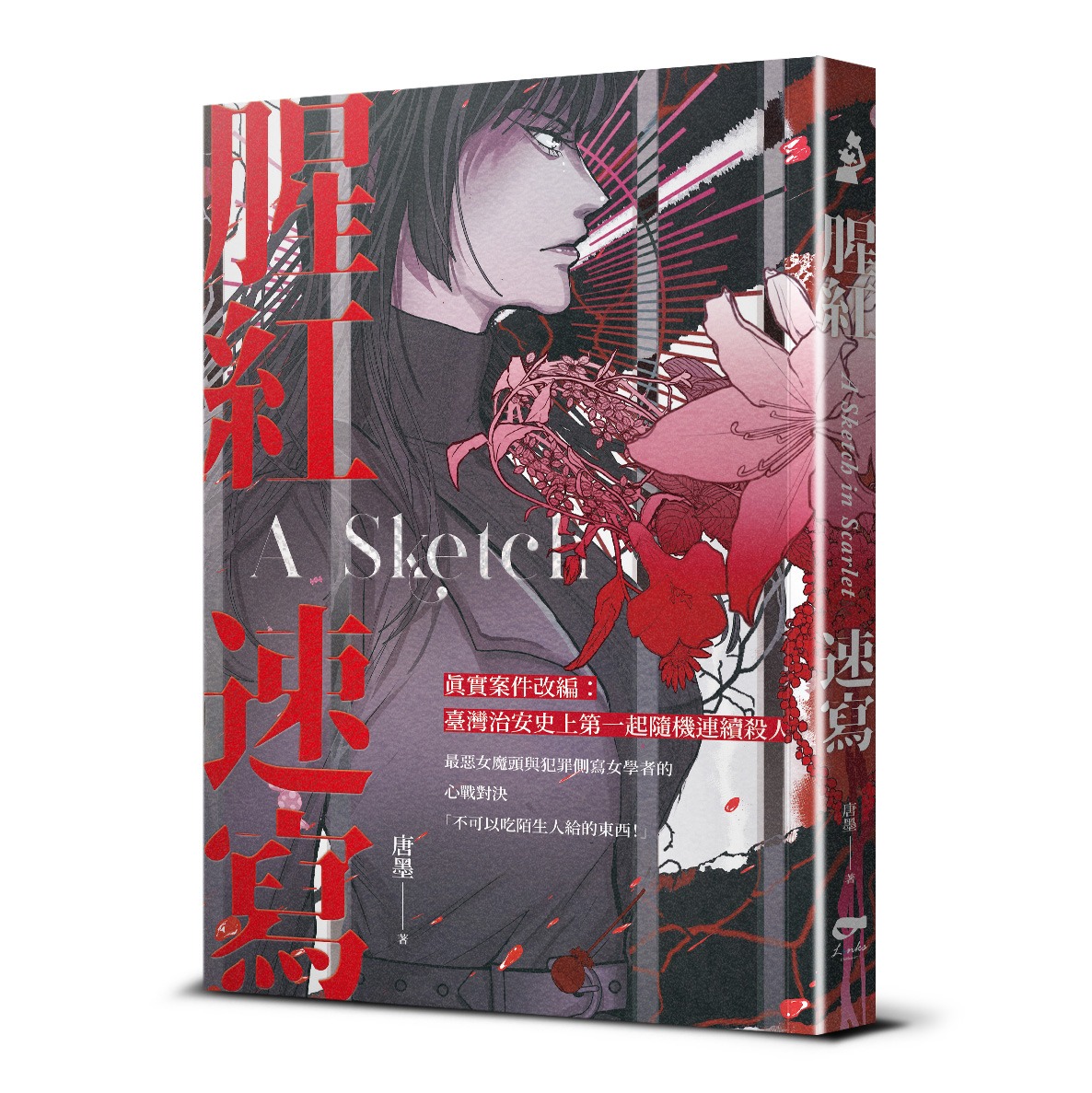
浮果《開著福音車徵廟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