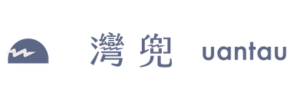編按:曾將台灣史結合推理小說寫出《清藏住持時代推理》系列的唐墨,甫上市的眾神民俗史——《臺北男神榜》;而他另一個創作面向,則是改編社會真實案件的非虛構寫作。書寫民俗與罪案,都需要大量的田調。本文邀請近三年跨縣市田調超過 30 次的民俗系作者浮果撰文,共同聊聊田調的美麗與哀愁,以及他們如何用田調與寫作貼近這片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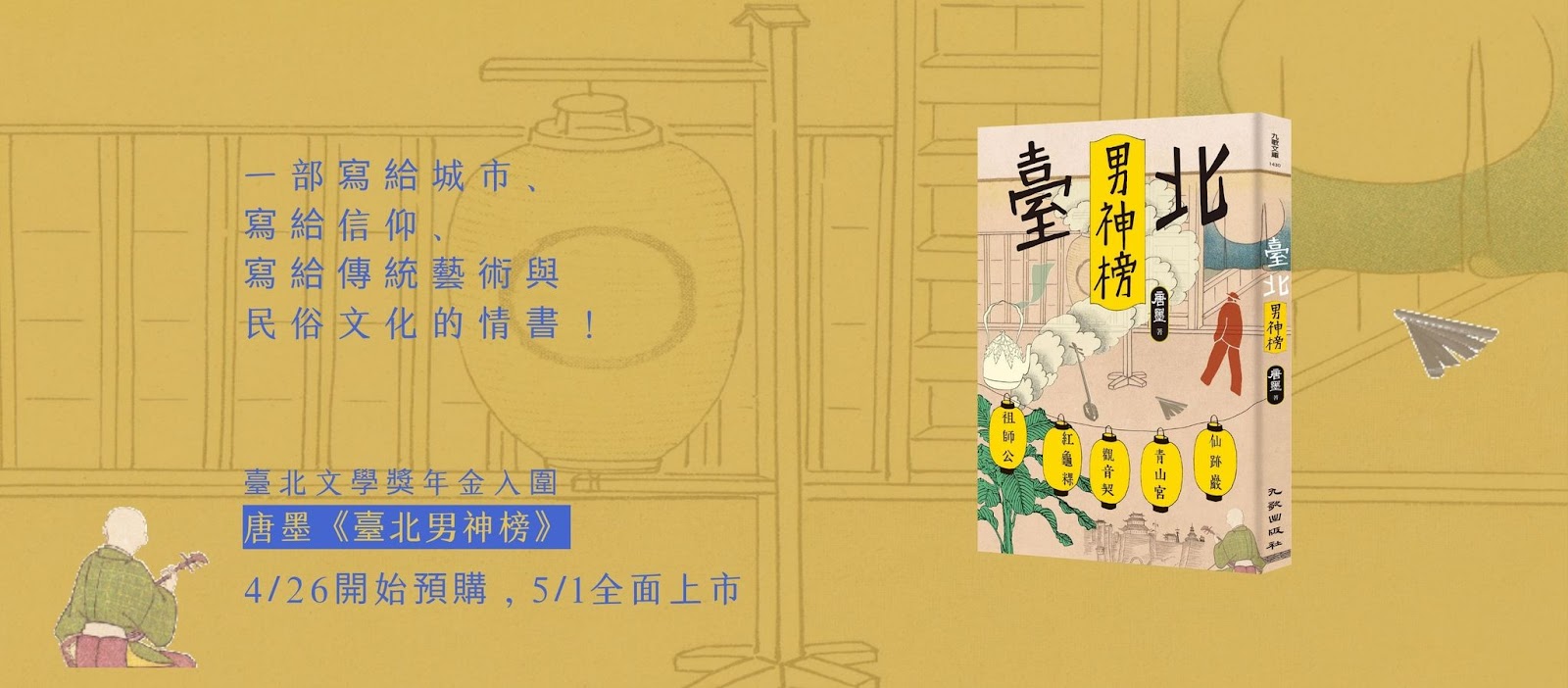
那年,在臺北文學獎頒獎典禮上,身為得獎者之一,坐在席位上等候,即使在場有朋友陪伴,社恐症還是快發作。這時一名男子身著華麗袈裟、手拿竹扇、談笑風生穿梭在全場,看他的樣子真讓人好羨慕,而那人正是以《臺北男神榜》入圍當年度文學年金補助的唐墨。
一晃兩年,唐墨再次真人出現在面前已經是相約於明星咖啡館。同樣是一身日本袈裟,不過這次沒那麼隆重,看得出只是常服,不過腳踩木屐,態度仍一派輕鬆。因為事前資料蒐集,知道他寫推理小說,在疑案辦擔任網站內容主編,大學兼課,對民俗也是略懂略懂,而且是真言宗的出家人。
各種殊異的身份,疊出唐墨給人的第一印象,有別於文學創作者的溫文儒雅,並不是說他沒有,而是他大鳴大放的性格更讓人印象深刻。
漫畫看著看著 就出家了
首先好奇唐墨幹嘛大老遠跑去日本出家?他説當然是為了瞭解佛法,而且是不動明王牽起的緣分。
唐墨最早是從日本漫畫《鬼神童子》知道不動明王的存在,這位在佛教密宗赫赫有名的五大明王之首,由於唐朝時期著名的留學僧弘法大師─空海將密宗帶回日本並創立真言宗的緣故,而成為佛寺中最常見的神明之一。
從尋找不動明王的資料接觸真言宗,順藤摸瓜找到真言宗在臺灣的道場,對道場主人運用心理諮商的理論解釋佛法及為人開解煩惱感到新奇,後來他決定前往該門派的大本營,位於日本和歌山縣的高野山,以見習生的身份參觀。

筆者曾去過高野山,千里迢迢去到那裡,即便不明白真言宗的教義,但對他們對待佛祖的態度印象深刻。最無法忘懷的就是僧人寒冬臘月著襪走在經堂裡頌念經文,作為觀光客才脱鞋片刻就已經冷到受不了,他們卻能為了修行甘之如飴。
唐墨以見習生的身份參觀,寺方雖然介紹導覽,可是箇中道理,若本身不具備僧人的身份,看什麼都只得表面,猶如走馬看花。這就好比上館子吃西餐時,大人告誡小孩使用刀叉要從外到內、器具得由小到大,你知道要照著做但沒有解釋原因,若要知道其中代表的禮儀與智慧則必須成為入門弟子才能獲得明師講解。
經過思考後,他出家了。而從這點就可知,追根究底是唐墨很重要的一項人格特質,如同採訪之前要擬提綱同樣也得深入瞭解當事人的背景,是一樣的道理。

《臺北男神榜》×《開著福音車徵廟公》:寫作,就是一條走回童年的路
出生於宜蘭員山鄉,這個以歌仔戲樹聞名、據傳是歌仔戲發源地的鄉鎮,對唐墨而言自然而言當然打小就接觸這門表演藝術,不僅埋下日後學習崑曲、南管的熱情,現在還主動在學車鼓的唱念。
「其實不只是受我爸出身員山的影響,我媽是外省人,外公祖籍在天津,而天津人喜歡看戲。以前流傳一個說法叫北京學戲、天津唱紅、上海賺包銀,意思就是當時你要學戲曲得去北京,學完了要去天津闖蕩名聲,可是真正可以被稱為一個角兒,得要上海人願意買單進場看戲才行。
外公愛聽戲,我媽也很喜歡,所以我從小就耳濡目染,加上我媽要照顧四代同堂的家庭,每天有忙不完的家事,小時候常放我一個人在樓上看電視,所以不只是歌仔戲,我四歲就接觸布袋戲。」

難怪唐墨採訪間聊到戲曲,表情眉飛色舞,原來是從小薰陶。這份熱情更融入到小說《深巷春秋》的創作,書中的五十五個章節參考崑劇《長生殿》下標,從清朝光緒皇帝與珍妃的相戀、寫到蔣中正與蔣宋美齡的相互扶攜再把場景拉回到唐明皇與楊貴妃的馬嵬坡斷情,呈現出三個女人截然不同的一生經歷。
除了戲曲、歌仔戲外,唐墨也從小接觸民俗文化,他不諱言在整理《臺北男神榜》稿件期間,讓他像是再走一次童年的路,許多小時候不解的事,逐漸在長大後獲得解答。
舉個近一點的例子,他在今年初目睹士林當地汾陽忠武王會(又稱郭子儀會)辦理慶典,回頭細查才知原來士林、板橋、社子、芝山過去都有姓郭的聚落,這才明白為何兒時搬到芝山小住,當時還在世的阿嬤堅持要買郭元益的餅,原來是跟此有關。

或是淡水九庄大道公信仰,大道公即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保生大帝,而九庄大道公是由淡水及三芝兩地九個庄頭輪流奉祀靠著丁口支撐的在地信仰,特色是有神像、無廟宇,靠兩只香爐代表神明,每年跟著爐主搬一次家。唐墨重新爬梳過去的回憶,這才意識到小時候就住在大道公遶境的路上。
筆者以民俗題材見長,自小生活在大同區這個散落宮廟私壇的舊城區,不僅看過不少廟會,外公在世時舞獅頭、扛神將,父親常年參與宮廟事務,耳濡目染下成了後來創作的靈感來源:

小說《八爺》將保生文化祭、城隍夜訪及青山王祭當成場景;《開著福音車徵廟公》則將傳統進香活動翻轉成臺灣版的公路旅行,童年的所見所聞有天也從毛毛蟲變成蝴蝶閃動在書頁上,真是始料未及。
儘管筆者現在對民俗充滿熱情,但青少年時期或許是受到新聞媒體影響或單純覺得宗教活動太LOCAL不夠酷,曾經有意識地裝做沒興趣,直到開始寫作,第一個閃過腦袋的念頭便是將喜愛的民間故事和神話融入現代文學中,直至今日仍不斷地挖掘出其中的趣味性,更加懷念兒時無憂無慮整天追著廟會跑的時光。
或許如同唐墨所言,寫民俗內容,是用成人的眼,再走一次童年的路。
《臺北男神榜》:信仰,需要一點魅力
寫民俗,不僅是文字上重溫一次童年;必要的田調,更是肉身的一次回訪,或者一次對異地的初識。
於筆者來說,田調很常時候是疲憊且無趣、甚至做白工的,但它的確是故事創作的基石。但越深入一處,越能感受物換星移,有一層隱約的危機感潛藏在後:這些事物終將消逝。

尤其民俗信仰面臨的還有認同危機。即使是近年已發展成臺北年末重要文化祭的青山王祭,仍有不少附近居民視為擾民噪音,唐墨認為,認同不夠是傳統信仰的危機,同時也是轉機。除了爭取外來移入人口的支持,在地人的返鄉回饋也能促成延續。「信仰不會消滅,但它會轉變,其中教育能發揮很大的力量。」
民俗的教育,需要的是耳濡目染的養成與習慣成自然。前面提到的九庄大道公信仰為了爭取年輕一輩能夠認同並加入行列,加入許多創意開發如彩繪大道公甚至推出「芝味季」數位展覽,讓更多人線上體驗。
文學人自問可盡的微薄之力,則是靠故事來行銷本土文化,讓神明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神像,而是充滿個性與魅力,例如《開著福音車徵廟公》中多管閒事幫信徒出櫃的王爺公,不禁也讓人開始期待唐墨筆下的男神們準備如何迷倒眾生。

神佛滿天,但真正落地生活的依舊是人。取材民俗的寫作,最終仍須將目光從神佛轉回至人間,寫出信仰與人的連結,寫出人的生活如何被信仰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