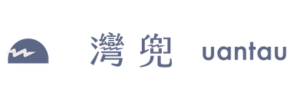疫情捲土重來,爆發得又快又兇。某日見朋友臉書發文,附上確診者足跡分佈圖,驚嘆雙北都已破百例確診,他住的大同區依舊足跡罕至,「難道是大龍峒保安宮保生大帝有保庇?」
短短一則貼文,讓我懷念起大同區來。我是從那裡開始慢慢認識台北的,也是第一個我以氣味記憶的城區。
在台北第一個租屋處就在雙連,一棟老公寓的分租套房,沒有窗戶,沒有陽台。雖是為了經濟考量不得不的選擇,但必須爬上四層蜘蛛網灰塵滿佈的樓梯、才能抵達的不到4坪暗無天日小房間,仍照護了剛踉蹌北上的我。
每日早上,我會走下樓梯,沿途經過雙連站旁的魷魚羹、大腸煎,迎面熱空氣都捧著碗鮮香帶醋酸味的羹湯直達鼻尖,旁邊的麥當勞相形失色。

炎夏八月,仍有穿著汗衫的長者或將襯衫解開兩顆鈕扣的上班族,非得嘗過一碗灑了香菜的魷魚羹,先逼出一身汗便不怕熱壞的一天。
再往前一間手工豆漿店,黃豆略帶焦味的暖暖氣味,刷掉了方才羹湯獨有的酸香;緊接而來是雙連市場攤販的吆喝、招呼、叫賣,天熱時不免錯覺自己像被丟進油鍋的地瓜球,跟所有人一起沸騰著:拖著小菜籃車挨挨擠擠的大嬸、汗衫掀至胸下腆著肚子的阿伯;旁邊正拍賣著些像是從工廠流出的廉價小家電,萬頭鑽動;樹下一位太太被簍簍橘子圍住,正向客人講價推銷。
我一身白襯衫西裝褲,每日非得在此滾過一輪(有時還會貪看小販口角險些遲到),方能抵達公司。好友怕我孤單,有時約了下班後見面,我們遊逛寧夏夜市,先在入口買杯甘蔗檸檬,擠入人群喝碗蝦仁蛋包湯,跟著排長長的隊換兩顆蛋黃芋餅;或者呢,買兩碗阿桐阿寶四神湯,就著阿伯滷味,回到我租賃的小房間,兩人邊聊邊吃。冬至那天,也湊興共食一碗熱呼呼圓仔湯、軟綿甜膩的燒麻糬。

相較於鄰近中山區的時髦文青,或者白領摩肩接踵的民權西路,雙連有種遺世獨立之感。類似南部家鄉的閒散節奏,充滿一種專屬於中老年的活力與朝氣,更率性一點,也更爽快一些,藕斷絲連間卻都是老街坊的情意。
職場菜鳥的我領著基本薪資,假日很少到鬧區看電影、逛街,多半睡到中午再到樓下早餐店買兩份餐,趿著拖鞋踱步回房間,邊看書邊吃。
是那種開在三角窗、隨處可見的早餐店,老闆夫妻約莫五十多歲,店面也是老老舊舊的,總飄著一股油膩的香氣。買久了,他們也會關心,不要老是吃吐司蛋餅。
閒聊間得知他們是從嘉義北上來打拼的(原來是北漂前輩啊)。某次跟家人去澳門旅遊,買伴手禮時算了他們一份。猶豫半天後趁打烊前刷洗爐台的時段,有點尷尬的送上。他們連番推辭後慎重地收下。隔了幾天再去光顧,正要掏錢被忙不迭阻止,說我送的餅非常好吃,拜託讓他們請一次早餐。

北漂仔的命運是無止盡的遷徙,工作因素我打算搬家。臨走前幾天,我下樓接過早餐時跟老闆夫妻說要搬走了,謝謝照顧。他們愣了一下,旋即說,要保重身體,有空再回去吃早餐。
後來我陸續又搬過幾次家,棲居過幾個地方,不免都有些過不去的心事。唯獨雙連,在記憶中總是蒙著一層昏黃暖色調濾鏡,氣味挾酸帶甜。我沒有再去光顧早餐店,很偶爾經過,站在對街看老闆夫妻如常煎蛋餅、抹醬,便覺得十分安心。如今仍莫名慶幸,第一個落腳處是雙連,它對人有種漫不經心的關懷,寂寞又溫馨,讓我在此學習如何自立。
本文刊載於〈城市學〉專欄,出處:《文化快遞》7 月號 no.25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