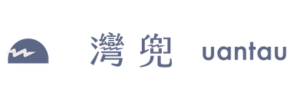涼冷天氣,只要不下雨,份外適宜步行。走路,特別容易觸及一座城市光明與黑暗的邊界。常常走著,經過富裕大廈再穿過擁擠平宅;巷弄裡有午後閒坐喝一杯咖啡的情調,也容得下白天喝醉倒地的頹廢。
曾經我也住在邊界上,很後來才發覺。以前住在文山區,對面就是某知名私校,上下課時間路邊常停滿名車。有次留意看,三分鐘內遍覽瑪莎拉蒂、賓利和藍寶堅尼。偶爾也好奇,那樣的名車坐起來是什麼感覺?
常在那條路走來走去,偶然見到其中一戶屋簷下總晾一排排尺寸小小的童裝。那數量,不太像一般人家。掛著小小招牌寫著「關愛之家」。記憶深層資料庫被輕輕撬動,一查果然沒錯,是專門收留照顧愛滋病患、落難移工及黑戶寶寶的機構。數年前,創辦人還因窮到偷奶粉而上新聞。
新聞報導,有些鄰里不諒解,不願與愛滋病患住在同個社區。幾乎每次經過,都只見到洗淨的衣物及毛巾晾成一株小樹,沒人吵鬧,甚至也沒有被收容者在外遊蕩。而我往往在門外東張西望,也不敢推門進去問需要什麼物資,怕打擾。最後仍只能捐點小錢,暗自希望他們不再被驅趕。
同一條路,往另一個方向走,是一條長長緩緩的上坡。路樹枝枒在風中輕輕搖晃,是個寧靜的社區,密密麻麻的窗並排,好幾戶窗上掛著塑膠袋,裝滿回收瓶罐;或者披晾潦草的衣衫。一早,社區旁食物銀行門口已出現排列隊伍;長椅上,時常有三兩人盤據聊天,有時提高音量像是口角爭執或講到興起,腳邊散落酒瓶。偶爾也好奇,腹裡多少冤屈,非得黃湯下肚才敢娓娓道來?

搬離木柵,偶然讀到報導者的專題〈台北市最後的貧民窟:安康社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驚覺以前日日行經的路段,曾是台灣收留越戰難民的居留地;同時也是為解決貧民居住問題,台北市最大的平價住宅。窮困與漂泊,兩瓢人生無以撫平的苦澀,在此落地生根;難民與貧民,最沒有選擇權的兩種身份,這裡是當初唯一的選擇。
數年前,安康社區改頭換面,蓋起嶄新的興隆公共住宅,希望讓低收入戶與一般居民混住。猶記當時還想去申請抽籤,卻因租金過高而作罷。恰好有個採訪入住興隆公宅居民的機會,正好進行一趟深入「賞屋」。依稀記得屋宅設計很不錯,明亮採光與良好通風,以及看來相當先進的智慧裝置。
受訪者是一對母子,媽媽是一位滿頭銀髮,氣質溫婉的老婦人,與開行銷公司的兒子住進公宅。顯然他們對於公宅非常滿意,老婦人開心分享常邀請好友來讀詩詞、做菜宴客,享受木柵閒適的生活。她坐著搖椅微笑望向窗外,半開玩笑地問:「跨年看得到 101 煙火嗎?」
後來常想起木柵發生的這幾個片段,短短幾步路,彷彿橫跨貧與富兩個世界。那條邊界十分模糊,並不是車子品牌或吃穿用度,而是走同一條路,居同一棟屋,有人只能顧及今天,有人則有過好每一個明天的信念。
本文刊載於〈城市學〉專欄,出處:《文化快遞》4 月號 no.26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