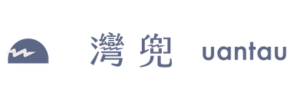數位遊牧民族大興其道的時代,移動工作似乎成了青年世代的某種渴望。真正意外的是,有一種角色也加入了這股浪潮——廟公。信仰看起來固定在香案、神龕與廟埕之間,但「少年廟公」楊庭俊,選擇以雲遊四海的方式走進人群,為各地信眾處理牽動命運的大小事。
在那之前,他其實是台灣記憶中最日常的那種「廟裡工作的人」。我們對「廟公」這個角色再熟悉不過,卻往往只停在表層印象:打掃、開門、泡茶、收驚、解籤。這份看似直白的職務,究竟包含多少沒被看見的工作?
而 30 歲的楊庭俊,為什麼會踏上這條修行路?又是如何在信仰與現實之間找到新的位置,讓一份傳統職務呈現出另一種更貼近時代的面貌,甚至變成一種「自由業」?
神明指定的環島旅行 解眾生因果也解自己心結
受訪當天,楊庭俊剛結束一場環島。這趟由宜蘭東嶽大帝開口的旅程,是一趟「解因果」之旅,解楊庭俊心裡的結,也解大眾的因果。沒有事先規劃,連出發日期都是神明指定,行程取決於「哪裡有需要就去哪」。
這趟「收驚之旅」,時常有人傳訊給楊庭俊,「你會路過xxx嗎?可以來看看我家人嗎?」他曾受託去為長輩收驚,順便為全家灑淨;也遇到有人求子,一查才發現祖上幾代都有夭折或倒房的狀況。
但他也強調,自己的服務屬於宗教民俗療法,鼓勵大家都必須先經過專業醫師診斷,有需要再尋求宗教協助。比如因果,就可能是科學無法觸及之處。
「要先了解家族的來龍去脈、祖先的經歷,再來決定要超薦哪位先人,會比較精準。」
這類涉及祖先的工作,往往得翻族譜、調閱戶籍、對照墓碑。過程既像宗教儀式,也像一場田野調查。
他還問了令我們大驚失色的問題:「你們有看過公媽龕嗎?」原來若祖先有過繼、入贅或倒房等紀錄,往往會被寫進「公媽龕」裡。
對仍保有神明桌的家庭來說,「公媽龕」或許是日常風景的一部分,但根本不敢去亂動,更別說意識到,那其實也是一座家族的微型檔案櫃。
對他而言,這份「靈性勞動」恰好與大學時期的訓練不謀而合,都是在追溯土地與血脈之間的連結。

大學開始幫人收驚 連基督徒都來求助
大學念人文地理,學習的場域不拘泥於教室,也常穿梭在公墓或田野,或者全班跟著老師去觀落陰。某次進香途中,他意外被「抓乩」被神點名,也被推入一場命運的測驗。
要不要當乩身,對當時的他而言,比填大學志願還茫然(現在回頭看,填志願或許還比較有方向)況且,這還是一場「父債子償」的契約,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的他,因緣際會在觀落陰的道場修行,同時師承已故爺爺的口訣,誤打誤撞開啟收驚技能,就連導生聚後續攤活動,也是幫同學集體收驚。
他笑說不知道為什麼同學常「出代誌」,印象最深刻是有位基督徒同學路過迎親隊伍,開始出現睡不好、吃不好、頭痛等症狀,求助醫生卻找不出病因,實在沒辦法了才來找楊庭俊,他判斷同學是被「喜煞」煞到,立刻進行收驚儀式。
基督徒可以收驚嗎?「當時大家對於不同文化都蠻開放的,而且臺灣人就是哪個好用就用哪個啊。」一款收驚技能,救了同學,還化解了宗教的隔閡。

宗教信仰在楊庭俊的經驗裡,並沒有染上太迷信的色彩。「也得神,也得人。」他說,當年正面臨職涯學業十字路口的學長,焦慮到每週都去觀落陰,想求神明給個明確答案,問到最後,被判官趕了出來。
信仰能安定人心,卻不能替我們做決定。類似的故事就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人生卡關時也常向東港鎮海宮線上求靈籤,求到王爺賜籤表示:「別再問了!」
唉,人就是這麼脆弱又倔強,明知道這條路就得自己一步步親自爬過去,卻還是希冀神明多賜予點信心和鼓勵,像爸媽哄小孩——沒事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104投履歷當廟公 當乩身也會遇到考考男
大學的經歷,早就預示楊庭俊不太可能走上公務員或工程師那種循規蹈矩的路。畢業後,他在 104 上找到一份「廟務人員」的職缺,正式成為全職廟公。
廟還在興建中,工作比想像得繁雜。他負責協助籌設社團法人,也包辦各項文書與行政作業。廟門一開,就是超精實的一天:早上六點開門、泡茶、做早課、引導香客參拜;晚上身兼會計結算香油錢,結束時往往已是八點過後。
這跟我們印象中看來清閒的廟公截然不同,薪資也較穩定還有勞健保,聽起來做一輩子好像也無妨。但修行之路從不順遂,一座廟就是一個道場,自然有很多讓你修行的地方,宛如一片江湖,也會有人心勾鬥,楊庭俊只好選擇離開。

家裡供奉的媽祖點明了:當乩童或出家,二選一!他曾短暫出家,進入佛教團體學習工作。
「(被抓乩後)有各種複雜的情緒,沒有人告訴你可以怎麼做,跟神明拔河的過程中,身心壓力都蠻大的,就是這時候接觸到佛教。那時覺得佛教沒有太多神意或通靈的概念,比較依靠自身智慧來應對事情。其實有點像希望躲進佛門世界,去避掉體質帶來的混亂。」
然而,佛門沒有磨掉他愛自由的天性,「如果換上袈裟,有許多需要幫助的人,可能會將他視為『師父』,無法用平等的身份對話。」幾經波折,他還是順著自己,也順從天意,脫掉袈裟回到俗世,為民眾消災解厄。
乩身雖被視為神明代言人,實務上可能更近似客服。楊庭俊說不乏有人抱著「我來考考你」的心態來問事,就想知道靈不靈。看來考考男不只存在於兩性關係,連神明都不放過。
但堂堂神明被考驗,難道不會起 tuh-lān(註)嗎?「神明的態度比較像是:你信,我才幫你啊。幫你第一次,可能是要讓你信服,如果一直不相信,那還是請你去找別人。」
說到「信」,有人就直接聯想到迷信。不過其實「信」常常是輕的卻篤定的。心頭煩悶時想去廟裡走走,在車上別上平安符,年初時為家人燒三柱清香祈福……臺灣人的信仰,多半是生活裡再日常不過的行程,而不是要傾家蕩產地追捧誰。
入世的雲遊四海 修行也要投保和投資
但這些信仰的日常,未必每人都能輕易取得。「有人覺得自己罪業深重,有人因為從事特殊職業而不敢走進廟裡。如果我只是一直在廟裡,就無法接觸到這些跨不進來的人。廟裡不缺人來做服務,我才用雲遊四海的方式,哪裡有需要,就到哪裡去。」
務實的問題來了,請他辦事有公定價或隨喜嗎?豈料楊庭俊早被神明指示要分文不取,還是得靠找些體制內的工作,才能維持雲遊四海的寫意,發展出各種斜槓技能。他會主持、表演、攝影,參與地方政府文化計劃,還當過牙醫診所小編做短影音,訪談當時還正在找工作。
雲遊四海不能只靠技藝傍身,還得做好風險管理。某次工作受傷後,促使他買了保險,最近更開始考慮投資。「我還是會用存股比較穩當的方式進行啦!」還好,否則如果他滿手臺積電,聽起來好像有點那個。
遊牧廟公的飄浪,不能美化成仙風道骨的浪漫,內裡全是現實世界鍛鍊出的肌力支撐著。就像你我一樣,想辦法踩穩每一步,只要活著,日日都是修行。
註:文中 tu̍h-lān 為臺語羅馬字拼音,唸音「賭爛」。因網站字型限制,部分變調符號無法正常顯示,故以較易辨識的形式呈現。